论文摘要:2019年年末,卡普尔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太庙同时展出,一时间各大媒体、专家学者、杂志期刊撰文报道,然而,直至卡普尔展撤展,几乎没有人说清楚卡普尔,这不免为卡普尔的中国之行留下遗憾。基于此,我想还是有必要再说一说卡普尔和他的作品。卡普尔的创作从始至终有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肉身”。这一定位可以从他80年代最早的艺术和建筑设计梳理,几乎涵盖了他从始至终的所有艺术创作。
关键词:肉身,卡普尔,梅洛-庞蒂
2019年年末,卡普尔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太庙同时展出,一时间各大媒体、专家学者、杂志期刊撰文报道,然而,直至卡普尔展撤展,几乎没有人说清楚卡普尔,这不免为卡普尔的中国之行留下遗憾。基于此,我想还是有必要再说一说卡普尔和他的作品。
卡普尔的创作从始至终有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肉身”。他的艺术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的装置作品,一部分是他的公共建筑设计,这两部分均是以“肉身”为主线展开,这一定位可以从他80年代最早的艺术和建筑设计梳理,无论是对孔洞和腔体结构的身体隐喻,亦或蜡和PVC材料对于肉与血的“世界之肉”的呈现,以“肉”为基质的定位,几乎涵盖了他从始至终的所有艺术创作,甚至他的《天镜》《下沉》《升华》等也与梅洛-庞蒂对“肉”的阐述密切相关,梅洛-庞蒂在讨论“世界之肉”与“身体之肉”等理论时运用了“镜子”“旋涡”“孔洞”等概念的论述,恰恰对应了卡普尔的大量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却鲜有人关注和说清楚。“肉身”是整个20世纪的重要议题,更是21世纪以来的20年当代艺术利用身体对抗拟像世界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卡普尔对于“肉”的关注和通过不同阶段的艺术创作一以贯之的呈现,是他在当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和价值的原因所在。
一、卡普尔与“肉身”主题
谈到肉身主线,我们可以从卡普尔的一个重要的展览切入,那就是2016年12月17日,卡普尔在罗马现代艺术美术馆(MARCO)举办大型个展,展览主题命名为“重新诠释肉与血”,展出卡普尔的30件创作,包括艺术家在2016年创作的《未诞生的》(Unborn)、《悬挂》(Hung)和《剥皮》(Flayed),以及2013年完成的《启示》(Apocalypse) 和《蒙难地》(Gethsemane)等等,其中24件以“重新诠释肉与血”为主题的作品首次展出。十年之后重返意大利举办大型个展,卡普尔选择用这样的主题别有深意。首先,证明“肉与血”的主题事实上一直是卡普尔非常关注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在他最早的创作中,对于性别和身体的隐晦表达,已经预示了他未来几十年艺术创作的走向。而这次罗马个展,卡普尔用“重新诠释”,说明经过多年的创作和思考,他对“肉与血”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展览中,红色依然是卡普尔作品最主要的色彩,艺术家想要探讨的是和“肉与血”相关的主题:直面生命、社会中的暴力与创伤。这些作品拒绝沉默且毫不避讳争议,观众会在作品面前感到战栗与对暴力及伤痛的沉思。


安尼施·卡普尔2016年在罗马现代艺术美术馆(MARCO)个展现场


安尼施·卡普尔,2016年在罗马(MARCO)个展,初乳First Milk
安尼施·卡普尔,2016年在罗马(MARCO)个展,剥皮Flayed
纵观卡普尔艺术发展的历程,他几十年来所关注的主题事实上是一脉相承的。从2016年“重新诠释肉与血”的个展,逐渐衍生而来,一直可以追溯到卡普尔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作品。从他早期利用颜色粉末堆砌的小型几何体的装置《白色的沙,红色的谷粒,和很多花》衍生而来,男女性别的隐喻和身体局部器官的表征逐渐植入他的作品中,如《一千个名字》《母亲如山》《处女》《无尽的柱子》《当我怀孕时》等,这些极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性器官的指涉以及对于“世界之肉”的呈现,在这些雕塑上往往可以发现类似孔洞或腔的结构,那是肉身与世界相通的路径,是物质与精神,肉体与身心的通道。极简的风格在卡普尔后期的作品中一直延续,但这些形体在卡普尔手中逐渐幻化出生命的潜能,作品对身体的隐喻与知觉现象学的理论密切相关,如《当我怀孕时》墙壁上微微突起的鼓包,以及《圣托马斯的疑惑》在墙体上简单划开的小口,《处女》堆砌的小山上的圆形开口,等等。卡普尔运用极简主义的创作方式,赋予了冰冷的墙体以人的温度。既有对女性和人类原初诞生的探讨,又有对宗教精神和教义的阐释。这些含糊不清的意义指向,构成卡普尔整体艺术创作发展的重要特征主线——肉身。


《白色的沙,红色的谷粒,和很多花》安尼施·卡普尔 ,1982年
《母亲如山》安尼施·卡普尔,1985年,北京太庙美术馆现场


《当我怀孕时》安尼施·卡普尔,1992年
《处女》安尼施·卡普尔,1988年


《一千个名字》安尼施·卡普尔,树脂,红色颜料,1982年
《圣托马斯的疑惑》安尼施·卡普尔,1989年
继20世纪90年代后期,卡普尔的大量创作也均是以肉身主题展开的,他善于利用材料质地本身的语言进行言说和表达,通过硅胶、半溶解的蜡和血红的颜色,通过灼烧、切割和机械运转创作出《自我生成》《向角落射击》《我的红色故乡》《为深爱太阳而起的交响乐》等经典的系列作品。而后期震撼人心的大型装置作品《玛耳绪阿斯》《奇异单细胞生物的截面体》以及《利维坦》等巨大的PVC皮的拉伸或放气都成为其作品实现的主要方式。这些作品均延续了卡普尔关于“肉身”主题的创作主线。


《未诞生的》安尼施·卡普尔,2016年,硅胶和颜料混合塑造出“血肉”效果,2016年在罗马(MARCO)个展,

《体内三部位》安尼施·卡普尔,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展,2015年


《宣召之三》安尼施·卡普尔,2014年
《宣召之二》安尼施·卡普尔,2014年
基于上述对卡普尔作品的回顾,可见其2016年重新诠释“肉与血”的展览并非凭空出世,由此可以继续梳理他的肉身作品线索。针对创作于2015年的《体内三部位》(Internal Object in Three Parts),卡普尔指出其蕴含“暴力、创伤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近些年欧洲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卡普尔对此并不避讳,直言作品与“人肉炸弹”相关。“我们生活在很糟糕的时代,人的肉身一直都是承受痛苦的载体,但现在却被政治所利用,”他说,“鲜血四溅、血肉横飞的画面很难从我的脑海中消除”。这件作品具有强大的情感冲击力。
这与2014年的《宣召》(Keriah)系列作品相似,表现的都是悬挂于墙壁上巨大且血淋淋的肉体残块,赤裸裸鲜红的肌腱与撕裂的肌肉。《体内三部位》也与卡普尔2002年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中心创作的《玛耳绪阿斯》具有相似的主题,均是基于古希腊神话中半羊半人的森林之神玛耳绪阿斯被阿波罗活活剥皮而死的故事。玛耳绪阿斯自不量力挑战作为掌管艺术和音乐之神阿波罗,输了比赛无端丧命。显然,卡普尔基于这一主题的创作,与撕裂的血肉密切相关。
卡普尔另一件关于《宣召》(keriah)的作品,具有相似的寓意。“Keriah”指犹太教徒在葬礼后一周内穿着破衣服的习俗,撕破衣服是挣扎的象征,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溯源,当雅各认出那浸透鲜血的衣服是他的儿子若瑟之物时,雅各从衣服上撕下一缕布条系在腰间,以慰丧子之痛。卡普尔通过肉与血的作品,打破传统宗教表现手法,再现了这一仪式的本质:肉与血宣泄着由内心撕扯导致的肉体痛苦。自14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许多艺术家有意将基督形象从宗教背景中脱离,将作品定位于人类受难的普遍象征。经历二战后,直到20世纪的肉身转向,以及进入21世纪的20年,艺术家们仍然受此启示,创作出大量无关信仰,意在历史的作品。
在卡普尔后期的作品里PVC材料得到了广泛的使用,PVC材料的性能为他作品规模和体量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条件。2002年,卡普尔为伦敦泰特现代艺术中心涡旋大厅量身创作了一件震惊视听的作品《玛耳绪阿斯》(Marsyas),该作品长160米,高35米,宽23米,横跨整个展厅的东西空间,作品以巨大的尺寸、抽象的造型以及纯粹的色彩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震撼,鲜红的PVC帆布又一次拉出大喇叭的形状,颜色艳丽、材质光滑,表面呈现清晰的纹理。该作品题目援引自希腊神话人物玛耳绪阿斯的名字,展厅中红色的膜寓意着他被阿波罗剥下的皮。庞大的PVC材质没有任何轻盈的质感,作品的题目和暗红的颜色使进入展厅的人们立刻感到作品中血腥的张力。连接三个大喇叭的鲜红色长筒长达155米,看上去很像人或动物的血管,也可让人联想到人体器官。



《玛耳绪阿斯》安尼施·卡普尔,2002年,伦敦泰特现代艺术中心
卡普尔在阐释自己这件作品时说:这件作品被三个大型不锈钢圆环拉扯开来——就像被拉扯开的皮肤一样。我想探索的是一种将机械语言转化成肢体语言的方式。作品最重要的是你不可能一眼看到它的全貌。整件作品基本是挤进涡轮大厅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只能看到它的局部。对于作品而言,它必须保持神秘性,不能一下子向外界展露全部。虽然这样可能让作品变得遥不可及,但我喜欢保持事物的神秘性。
就算我们不曾听说过玛耳绪阿斯的故事,观众仅从泰特现代美术馆看到卡普尔《玛耳绪阿斯》作品,已经很容易从视觉的直接经验中感受到它震慑的能量。无形的力量拉扯着它们的肢体,无声的呻吟像哀怨的音乐响彻场馆。而当我们了解到玛耳绪阿斯具体的神话内容后。卡普尔作品中的“音乐”和“血腥”的意义又获得了文化与历史深度的内涵,卡普尔坦言:我想将肉体悬置于空中,使玛耳绪阿斯直接冲击观众的试听感知,把他们带入一个纯粹的领域。观众无法从任何方向看到完整的雕塑形体,只通过一连串离散的感观进行拼凑,这样反而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性和探索的欲望,作品让人充满从此端向彼端张望探寻的冲动,而从每个端口望过去都会获得特殊的视觉感受,使我们永远都身处其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但却永远无法将它尽收眼底,作品选择庞大体量的方式正是对观众常规欣赏作品方式的拒绝。


《我的红色故乡》安尼施·卡普尔,2003年
《我的红色故乡》(局部),安尼施·卡普尔,2003年
对于身体和血肉的表达,使卡普尔选择了红色,红色成为卡普尔最频繁实用的颜色。红色显然是血液与身体的颜色。它是地球的颜色,而不是太空的,他认为红色所揭示的黑暗比黑色与蓝色更为深刻和浓重。2015年,卡普尔在莫斯科举办的个展“我的红色故乡”中运用了大量的红色,展览题目依据被展示的主要作品命名:《我的红色故乡》(My Red Homeland)。该作品是2006年米兰展中的经典作品之一。红色的巨大蜡块常在卡普尔的作品中被频繁使用,红蜡具有透明感和肉的特征,它被放置在一个圆形且冰冷的金属装置内,伴随发动机的运行,其中的金属臂围绕中心轴缓慢旋转,红蜡被反复碾压形成周而复始的深沟,血红色的蜡块连接着历史的残酷记忆并延伸至原始祭祀的仪式,红色的形态通过反复的辗轧被不断地解构与重塑。作品形态的冷酷与恒定的行为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试听体验,迫使观者凝神驻足进而唤起对现世与未来的深刻思考。
蜡,是杜尚和博伊斯都曾热衷的材料。蜡在60度即可溶化,并可与不同色彩混合形成不同效果。蜡的透明感与柔软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皮肤和肉,它是制作蜡像和人体雕塑的最佳材料。卡普尔钟爱使用蜡同样是基于它的特点,他将蜡与红色油彩混合,蜡的生命体特征由此被激活,成为其艺术创作中的特殊材料语言。卡普尔常将红蜡与动态装置相结合,力图引发与观众情感的强烈互动。如《我的红色故乡》《斯维岩》《向角落开炮》以及《为深爱太阳而起的交响乐》等作品,着力突显物质的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刻意对制作过程的强调与布置,可将观众引入对材料本身的感悟。相比冰冷和静态的极少主义作品,卡普尔赋予了作品全新的活力与生命。
对卡普尔而言,红蜡成为一种对肉与血的隐喻和变体。2007年《自我生成》(Svayambh) 。“Svayambh”在梵语里是“自我生成”或者“自动生成”的意思。卡普尔非常欣赏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电影《逃亡火车》,这无疑为作品的诞生埋下潜在的影响。《自我生成》主体重达40吨,高3米,由蜡、颜料和凡士林混合而成的矩形状红色蜡块,像车厢一样被安放在移动的轨道上,以一种几乎感觉不到的速度移动,在法国南特美术博物馆5个展厅之间贯通的轨道上缓缓行驶。作品像受伤的列车,勉强地穿过拱门,由于蜡块总是要比门框略大,所以每次在通过的时候总会被刮掉一些,留下一路血红和喷溅的痕迹。一次次残忍的刮蹭,从而形成自我生成的创伤。


《自我生成》安尼施·卡普尔,2007年,法国南特美术博物馆
卡普尔的《向角落射击》与《自我生成》异曲同工,均以红蜡为媒材并注重心理层面的探索。2009年,卡普尔荣幸的作为第一个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呈现了他艺术生涯以来的重要作品以及一些新作。其中包括水泥雕塑以及《向角落射击》(Shooting into the Corner)的装置,一门大炮不断的将蜡块发射向展厅的墙角,喷射到墙面与地板上的红蜡被击碎,喷溅并慢慢流淌渗透,伴随每一次射击时扣人心弦的一瞬,展厅瞬间变成惨烈的战场。作品充满了戏剧性,激发起观者的想象。《向角落射击》与《自我生成》作品的意义指向一脉相承,暴力、对抗与血映射着人类漫长历史流变中的暴力记忆。作品与观众的互动,以及与不同场域空间的对话,形成集体意志与艺术家个体情感的共振。卡普尔试图使作品生成某种体验,使观者身体经历和体验的过程成为内化入心理的过程。

《向角落射击》安尼施·卡普尔,2015年
2013年,卡普尔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展览馆”举行大型个展“卡普尔在柏林”,此次展览被视为是卡普尔长达30年艺术创作生涯的顶峰,是一场色彩、形体与材质的盛宴,以致英国策展人诺曼·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将其称为“一座让人目不暇接的雕塑剧场。”个展在美术馆18间展厅中展出,共70余件作品,卡普尔介绍展览时表示:展览有一大半都是新品,当然这是一种冒险的做法。但我就是喜欢干这种傻事。战场好似是卡普尔的雕塑“操舵室”,充满了闪亮的戏剧式的作品。
卡普尔为该展览特别创作的作品《为深爱的太阳而奏起的交响乐》(Symphony for a Beloved Sun),在美术馆中庭展出,四个类似建筑工地的传送带腾空架起,载着巨大又粘稠的红色蜡块穿过墙上的洞口和地上的活板门向上移动,被有序地送到高坡,金属管的传输轴上挂满了红色的残迹,在移动的时候发出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像经过屠杀后的血迹,蜡块最后在传输带尽头坠落,啪的一声摔在地板上。其旁,一个巨大的红色“太阳”被脚手架撑起悬在半空,俯视着周围。独自走在展厅中,马达的呼呼声和蜡块砸落的声音响彻美术馆的中庭。而蜡块材料不断的聚集,感觉像是具有祭奠的仪式。
格罗皮乌斯美术馆的建筑空间也不断地增强着这种仪式般的氛围。该美术馆位于一座典雅的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内。二战期间,该建筑曾遭到破坏,直到1981年重新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毗邻该建筑物的正是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司令部的旧址。从格罗皮乌斯美术馆的窗户向外望去,便能看到贯穿整个冷战时期隔离西方与东德的柏林墙的一段。当卡普尔来到该展厅进行创作时,他试图打破场馆带有叙事感的顺时针展览参观路径,并将展厅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每一空间都展示着他不同阶段的创作,而这些作品都令观众不断地联系起在中庭的那个巨大装置。


《为深爱的太阳而奏起的交响乐》安尼施·卡普尔,格罗皮乌斯美术馆2013年
《为深爱的太阳而奏起的交响乐》(传送带局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厅现场,2019年
在所有新作当中卡普尔本人最喜欢并且认为它充满了“狂野又疯狂想象”的是那条漏气鲸鱼,这条用PVC材料做成的鲸鱼被命名为《利维坦之死》“The Death of Leviathan”(2011-2013),作品非常显眼,占用了三个展厅,这个放了气的PVC材质的气球似乎是卡普尔在巴黎大皇宫展厅的那件充气作品《利维坦》(Leviathan)的另一个版本。而材料本身释放出的刺鼻味道让人不禁幻想海底怪兽“利维坦”慢慢腐烂的气味。它承担起卡普尔参与社会重大议题的语义。这是一具漏了气的巨大皮囊,就像一头已经死去的庞大鲸鱼。他说:霍布斯认为国家就像巨兽利维坦掌控着每一个个体,而利维坦的死亡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死亡或者凋敝,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现在都是这种状况,所以个人不得不承担起原来由国家承担的那份责任。
二、卡普尔与梅洛-庞蒂
本次卡普尔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了数十个尚未完成或已经落地实施的建筑和大型装置模型。很多观众围着展台走来走去,有的人并不感兴趣,有的则觉得这些模型很奇特,但并不得要领。其实卡普尔的这些建筑和装置模型,绝大部分与人的肉身以及器官的隐喻相关。通过卡普尔的提炼与概括,结合建筑结构和落地区域的特点,使得这些具有肉身隐喻的作品与周围的世界和大众的生活紧密结合。卡普尔通过作品对“身体之肉”与“世界之肉”的呈现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梅洛-庞蒂对于“肉”的理论诠释。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他被称为“无可争议的一代哲学宗师”。 “肉身”成为梅洛-庞蒂晚期哲学关注的核心概念,从1959年起,梅洛-庞蒂开始使用“肉”这一概念,他对其较为频繁的使用主要集中在1960年的笔记与手稿里。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梅洛-庞蒂对“肉身”概念做了全面的描述,他所提出的肉身概念预示了其后期哲学的新方向。他的肉身哲学以“世界的肉身——身体的肉身——存在”作为核心展开,以此进一步阐明了身体和世界的同质性,同时用肉的绽出来回应意义和表达的难题,并在“世界之肉”的基础上,提出“自我与身体”之间相互“交织”的可逆性关系。
在20世纪思想史上,梅洛-庞蒂第一个明确了“肉身”概念的哲学意义,他描绘出这种“我们称之为肉的东西,这一内在运作的团块,在任何哲学中都没有它的名称。”的内在存在,因为其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实体,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其中每个身体、每个事物都仅仅作为与其他身体、其他物质的差别而出现。“肉”成为梅洛-庞蒂进入其后期存在论思想的一把钥匙。他大大拓宽了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肉”不仅用来描述我们的身体,也可以用来描述可见的外部事物,亦可以用于语言、时间、历史与存在等抽象概念中。
恰如梅洛-庞蒂指出的,传统哲学中不仅没有“肉”这一概念,甚至未有可以用来阐明它的其他概念。肉是一种存在元素,是一种基本的织料(étoffe),它由此展开了一幅开放的永不会完成的织锦(tissu),始终处于开裂或构织状态中的多形态的织锦。由此,我们不但可以认为,身体是由“肉”构成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都是由“肉”构成的。对于梅洛-庞蒂三个层面的肉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和领域研究卡普尔的作品。通过哲学家和艺术家关于“肉”的探寻,我们可以深入地感受到人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深刻思考。
(一)卡普尔与世界之肉
作为原始母体的“世界之肉”,其本身是浑然一体的,其中,人和所有其他的存在物尚处于感性存在的未分化状态。但此时,这个整体却出现了皱褶(pli),其中的部分开始从其他结构中摆脱出来,像图形从背景中凸现出来一样,类似自然之光从黑暗之渊中涌现。这便是“存在”(Être)的最初“开裂”,是世界第一道“光”,是源初的“有”(ilya),也是意义的原始呈现。这亦是人的诞生过程,是可见世界得以显现的过程。随同“世界之肉”的开裂,出现了原初的视觉与触觉。即感知是与世界一同诞生的。卡普尔的作品《升华》《下沉》《天镜》等作品,利用光的反射,气的升华吸入孔洞的过程,水的旋涡下沉孔洞吸入地下深渊的神秘,用可见的物质性呈现了梅洛-庞蒂对源初的“有”(ilya)的阐释。
固然,在构思一种新的存在论哲学时,“肉”不可能是唯一的概念,与它处在相同地位的概念还有“自然”“存在”“大地”与“世界”等。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世界”这一概念,它与我们曾提到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世界”并非处于同一层次。抑或说,梅洛-庞蒂在其后期哲学中使“世界”具有了双重的含义。它时而指的是可见者的总体,在此意义上,它仍然是与人相对的;但有时它又常被看作是基本的母体,即本源性的存在。从此意义上看,世界时常被称为“垂直的世界”“存在的世界”与“荒蛮的世界”等,它可以与“自然”“存在”与“肉”大体同义。由此,“肉”这一概念也时常被称为“世界之肉”。
上文所描述的卡普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基于梅洛-庞蒂“肉”的理论展开的,蜡和PVC材料成为卡普尔构建“世界之肉”的基本的“织料”,它由此展开了一幅开放的永不会完成的“织锦”,他的《玛耳绪阿斯》《我的红色故乡》《向角落开炮》《自我生成》其中PVC的拉扯,蜡被搅拌和运行投掷,均使作品始终处于开裂或构织状态中,形成多形态的织锦。卡普尔将这些可见的物质性材料转化为世界与人的一种同质性的存在元素——肉。


《非物质(尖顶)》 安尼施·卡普尔,2007年,2019年北京太庙展览现场
《S曲线》安尼施·卡普尔,2006年,2019年北京太庙展览现场


《狭板》安尼施·卡普尔,2013年,2019年北京太庙展览现场
在梅洛-庞蒂后期的遗稿中,他通过“肉”的“镜子”现象,融入视看中“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条在世界之肉的存在论意义上,自我和他人之间“交织”关系的通道。梅洛-庞蒂用视觉举例,指出不存在我与他人的难题,原因“不是我在看,也非他人在看,而是一种无名的可见性停留在我们二者之中,一种视觉按原始性质隶属于肉,在此时此地向四处延伸,既是个体,也是尺度与普遍”。从之一角度看,卡普尔的许多装置作品选择运用打磨得光亮的不锈钢镜面材料绝非偶然,他不但对知觉现象学理论有着深入的理解,同时运用艺术的视觉语言,对其进行了完美的呈现,使作品与“自然”“存在”“大地”与“世界”交织,在彼此交融中将观众映入作为物质媒介的作品中,将肉质的身体与世界通过各种镜子型态,在不同场域空间中交融在一起。
梅洛-庞蒂在其研究笔记《触-被触,看-被看,身体,作为自我的肉身》(1960)中写道:“肉身是镜子现象,镜子是我与我的身体关系的延伸。”在同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眼与心》中他指出:“镜子出现在从能见身体到可见身体开放的回路中”即是说,镜子现象能够出现的原因,在于身体具有作为能见可见者的自反性,即“一种感性的反身性”。而肉身镜子的功能就在于其可以复制和传达这种自反性,并向我们呈现出自己在视看中无法获得的东西,也就是在我看的背后的不可见者,或是在他人目光中的我的形象。“肉身镜子”理论恰好补充了我的经验无法触及的“不可见者”,此不可见者是表象存在与感性存在的片段,是既属于我自身又不属于我自身的本质存在的片段。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肉身镜子进行自触与自看,向自我开放,将我们陷入朝向自我的纯粹自恋。而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镜子,不仅不能达到自我反而是在逃避自我与忽视自我。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一个开放的通道,可以使自身转化为表象的片段与感性的片段,同时朝向自己以外投射出去。
在本次太庙的主展厅中,卡普尔安置了他的大量镜子系列作品,有《倒置的世界》《C形曲面》《狭板》《S曲线》《非物质(尖顶)》 等,这些作品利用不同型态的镜体表面的反射,使观众在镜子里所投射的自己呈现各种变形的状态,古老的中国建筑太庙内的空间环境也映射在镜子中,与观众的身体在作品内部通过变形的呈像,交融扭结在一起。每件作品有不同的变形扭转,使观众站在作品前非常诧异作品内部的自己,当用手机拍照时,由于不同角度的光线折射,照片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型态。通过卡普尔的肉身镜子我们可以进行自触与自看,陷入朝向自我的纯粹自恋。而在变形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开放的通道,可以使自身转化为表象的片段与感性的片段,同时朝向自己以外投射出去。此时我们不只是通过镜子得到了我的身体的不可见性,同时又向镜子出借了我所拥有而他人不能拥有只能视见的那一部分,我在镜子里可以看到我的身体具体视像的反面,也是我的身体的镜像知觉的反面。


《角落消失在自己的内部》Corner disappearing into itself
安尼施·卡普尔,2016年罗马展现场
通过梅洛-庞蒂对于肉身镜子以及“世界之肉”概念的分析与解读,卡普尔的选择镜子作为装置作品的媒介材料可谓别有用心。在《角落消失在自己的内部》的镜子装置中,镜子呈现了类似人体性器官的型态,在挤压中,消失在墙角的肉质世界里,在镜面的反射下,我们还可以依稀看到镜子作品中所折射的外部世界,角落的镜子成为连接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通道。
卡普尔解释说:“对我来说,打磨表面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它达至完美时,就会升华至超越物质性的一些东西。” 他将这些作品称为“非物质”,内部的几何构造与反光材料共同构建了对具象的瓦解。卡普尔最著名的镜面钢铁作品,包括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巨型《云门》;凡尔赛宫的《C形曲面》和洛克菲勒中心《天境》等,其共同点在于突出的曲面与迂回的外表面凹凸有致,既有内向折叠亦有外向延展。像梅洛-庞蒂对于“皱褶”的论述,卡普尔所打造的这些扭曲形态为观者提供了一幅观察世界源初状态的镜像,光线仿佛被空间扭曲,而我们的感官亦仿佛内外倒置,感官的表面仿佛游弋在自我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中空地带。


《天境》安尼施·卡普尔,洛克菲勒中心,2006年
《C形曲面》(C-Curve ) 安尼施·卡普尔,法国凡尔赛宫,2015年


《天镜》安尼施·卡普尔,英国伦敦肯辛顿公,2009年
《云门》安尼施·卡普尔,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2004-2006年
(二)卡普尔与身体之肉
梅洛-庞蒂指出, 我们可以将感觉的产生看作是“肉”的第一次开裂,它将“身体之肉”从“世界之肉”中独立出来,所以“身体之肉”与“世界之肉”像图形与背景一样可以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但“肉”的运动并未止息,其仍在身体之肉中做再结构化的重组活动。这可以看作是“肉”的第二次开裂,其将我的身体本身一分为二,在我的“身体之肉”中出现凹陷和窟窿,即 “漩涡”,一种“虚无”,这便是心灵和意识的出现,一个人称性的“我”的诞生。如若从个体发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感觉的产生是伴随婴儿的降生而出现的,且自我意识的出现则始于婴儿期六个月左右时的对镜观照,心理学上称其为“镜像阶段”。儿童在此时开始发现了自我,由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卡普尔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孔洞的形式,本次中央美院展厅中的数十个模型,是我们了解卡普尔艺术创作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卡普尔对于肉身的提炼与艺术语言的转化过程,作为公共建筑设计,均需要人的使用和通行,所以在这些建筑模型中,均有各种型态的孔洞设计,这些孔洞是公众行走的通道,也是卡普尔以“肉身”为基质,将人引向“世界之肉”的方式。这些日常生活的公共场景中,孔洞充满着诱惑力,人的身体孔洞成为其介入肉质世界的通道,也可以成为肉身逃逸的路径。
通过梅洛-庞蒂的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卡普尔的艺术,在其早期作品《当我怀孕时》《一千个名字》《处女》《母亲为山》等作品中,以及后期的公共建筑设计《景观模型》《肉体》《尾亭》《但丁》《蒙特圣安杰洛大学地铁站》《图拉真地铁站》等,对于女性性器官“孔洞”和腔体结构的表现,呈现了卡普尔对于我的“身体之肉”中出现凹陷和窟窿,即心灵和意识的出现,一个人称性的“我”的诞生。唯有身体个体从可见者整体中脱离、独立出来,它才能被这一整体所包围,才能有它自己的意识;反过来,唯有当意识出现时,这一身体,一个个体与其他可见者整体的分化过程(differentiation)才算最终完成。


《景观模型》(侧面)安尼施·卡普尔,1990年
《肉体》安尼施·卡普尔,2002年

《尾亭》(侧面)安尼施·卡普尔,2005年


《蒙特圣安杰洛大学地铁站》安尼施·卡普尔,2002-2008
《图拉真地铁站》安尼施·卡普尔,2002-2008
与卡普尔的孔洞相对,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谈到的“窟窿”概念,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人的身体像一个“漩涡”,“我的世界受到吸引和被吸入”。他人的身体之所以会是“漩涡”,是因为他的身体之肉和我的身体之肉一样有一个“窟窿”(意识),它需要作为可见者的我去填充。同样,当我形成了自己的意识,从其他可见者中脱离出来后,会很容易陷入“沉默的唯我论的世界”,而此时,他人的目光会使我重新和可见者发生关系。通过他人的眼睛,我们又可以对自己变得完全可见了,我们眼中的空隙和我们的背后的孔洞重新又被可见者所充满。卡普尔的《下沉》和《升华》将孔洞设置在伸向地下的深渊和上升至无尽的天穹,在神秘和深不可测的不可见中,使观众跟随作品被吸入孔洞,随即消失,促使精神意识从肉质身体中出离,进入那个不可知的“窟窿”(意识)中。


《下沉》安尼施·卡普尔,法国凡尔赛宫,2016年
《下沉》安尼施·卡普尔,北京红砖美术馆,2015年



《升华》(Ascension)安尼施·卡普尔,威尼斯圣乔治大教堂展览现场


《升华》安尼施·卡普尔,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现场,2009年
与《玛耳绪阿斯》巨大的震慑效果相似,2011年在巴黎大皇宫,作品《列维坦》同样使用PVC材料制作,像一个充气的大皮球,在充气后形成高达38米,内部体积达到7万2千立方公尺的弧状球体,而大皇宫的门成为人们进入肉质世界的“孔洞”。《列维坦》“leviathan”该词源自《圣经》,指的是曾出现在圣经等西方经典里那个吞咽了约拿的大海怪。而如今它化身为大皇宫内膨胀的巨型气球,此刻巨兽的意象更为鲜明。从外部看庞然巨物呈黯黑色,鼓胀且彷佛在缓缓呼吸。而从震动着的内部观看,借助外部光的透射,作品内壁泛着暗红色并呈现错综复杂的线条与光影叠映的效果。PVC皮在此又一次成为对生命象征的体现,皮肤的质感与冰冷的建筑空间相呼应。


《利维坦》安尼施·卡普尔,2011年
《利维坦》(内部)安尼施·卡普尔,2011年
卡普尔常利用强化身体局部形态或分解抽象结构突出性别寓意指向。如象征阴道的黑洞或膨胀的子宫等。具象内容与形象的禁锢,进而将观众的关注点引向作品的材料中。2009年,卡普尔作为英国布莱顿艺术节的首席艺术总监为艺术节创作4件雕塑作品,其中最大型的装置被命名为《肢解圣女贞德》。他没有将“贞德”塑造成完美无暇的战士,而是用两堆红色的山丘以及一个凹陷的红色土坑,还有两个不规则的横向柱体,象征了“贞德”的乳房、子宫以及被肢解的大腿。大量的红色颜料被再次使用,对卡普尔而言,“贞德”是具有母性象征的生育图腾符号,其身体是可供人们栖息的凹陷洞穴。神话使一些东西变得不朽,它比纪念碑更鲜活,因为它们总是在不断变化中。


《肢解圣女贞德》安尼施·卡普尔,2009年
在本文开篇提到的2016年罗马个展“重新诠释肉与血”的展览中,卡普尔同样展示了他的PVC作品《奇异单细胞生物的截面体》(Sectional Body preparing for Monadic Singularity)。这件作品也在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展厅中展出,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立方体,却在内部与外部的连接中充满玄机,围绕作品从外部环绕一圈,每个立方体面上都有一个型态不同的孔洞,使立方体的内部空间与自然或展厅的外部空间融通。步入内部后,会立刻被红色拉伸的PVC材料所震撼,在各种孔洞投射的外部光源的映衬下,这些红色PVC充满了血色和肉质的特征,当观众穿梭游走在一肉质空间里,仿佛进入了人类身体的内部,亦或世界之肉的内部,这种感受与在巴黎大皇宫的《利维坦》以及伦敦泰特美术馆中的《玛耳绪阿斯》的肉质拉伸具有非常相似的感受,即对于自我与肉质世界的理解。


《奇异单细胞生物的截面体》安尼施·卡普尔,2015年
《奇异单细胞生物的截面体》(内部)安尼施·卡普尔,2015年

《肮脏角落》安尼施·卡普尔,2015年,巴黎大皇宫
2015年卡普尔在巴黎大皇宫实现的《肮脏角落》(Dirty Corner),一个巨大、锈迹斑斑的金属“阴道”出现在凡尔赛花园,也是对身体与世界孔洞的生动诠释,它始于一个9米高的近似椭圆的入口,逐渐收缩最后结束于黑暗,四周不规则地散置着十吨重的石块,仿佛地震遗迹,或者战争残垣。卡普尔制造的洞穴或缝隙,常常被理解成女性阴道的象征,傲然盛开,吞噬观者。在卡普尔的概念里 “性”是人类内在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乎欲望,关乎动机,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起源”。卡普尔从早期创作中便开始关注“起源”的概念,以形象化的直接意象来表达他对“起源”的感受,红色颜料对材料的形态进行渗透,展现生命原初最本质的颜色。这些作品鲜红如血,分娩时的鲜血,女性的经血,肉体破裂的伤口,生命逝去剩下的凝结血块。


2018年卡普尔巴黎个展“another (M)other”展览现场
2018年卡普尔巴黎个展“another (M)other”展览现场
2017 年,卡普尔在伦敦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举办展览。此次主题含有三个关键内容:跨越表象的内廓、皮肤、叙事性的诗人思想。卡普尔指出,该展览所有的新作都是有关“皮肤或物体表层的叙述”。这一主题并非是指艺术家专注于物质表面的叙事,而是力图通过对现实物体层层地解剖,进而揭示其表层之下的深刻寓意。
2018年,卡普尔在巴黎个展“另一个母亲” (another (M)other),将英文字母M去掉,展览题目就可以称为“一个,另一个”在此,卡普尔指出,母亲的含义是多重的,她指代着一个族群的起源,亦是人类的起源。在展厅中,一个类似女性阴道的大型装置从一个展厅横跨另一个展厅。展墙上悬挂着卡普尔具有标志性的圆形镜面,但这次的镜子被血色侵染,同时两个圆镜子并置在一起,象征着女性的乳房,与伸进展厅的半截类似阴道的装置组合,呈现女性的符号隐喻。这样的作品可以让我们联想起《肢解圣女贞德》的作品,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卡普尔的极简风格作品《当我怀孕时》,镜子和孔洞形态的组合,也成为对梅洛-庞蒂“肉”的理论的深刻诠释。
三、20世纪的肉身转向
“肉身”作为战后以来非常重要的核心议题,事实上与20世纪初以来各阶段的哲学思潮有着紧密的关联,也是本文得以展开和讨论的时代背景。身体是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社会、政治和历史等各个领域。20世纪以来,众多哲学家聚焦“身体”概念:快感、欲望、力比多和无意识等形成“身体”之下的各种分支主题。从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到弗·詹姆逊、巴赫金、吉尔·德勒兹以及伊格尔顿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梳理“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二元论的身体与灵魂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思想逐渐式微,身体成为无法忽视的物质实体浮现在理论视域。这些思想共同影响和建构着当代艺术的创作。
战后以来,身体艺术占据了当代艺术中极其重要的位置,当代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聚焦身体问题,身体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的表达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交错,同时与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交汇在一起,呈现人类对“肉身”更深入的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普尔的所有艺术创作几乎全是基于“肉身”的基础展开的,他对红色的痴迷,对“肉与血”主题的再诠释,与宗教、文化、哲学、心理学、符号学以及整个20世纪众多哲学理论关于肉身主题的探讨密切相关。他用各种物质性的媒介材料:蜡、PVC、镜子、水、孔洞、旋涡等开启了当代艺术对于肉身的全新解读和呈现。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成熟艺术家的卡普尔,从始至终以“肉”为基质的清晰的艺术脉络发展线索,正是基于此,确立了卡普尔在世界当代艺术舞台上不可否认的影响力与价值。

作者简介:
范晓楠,清华大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艺术评论人,策展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艺术思潮和视觉文化研究,著有《景观社会的图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绘画研究》《肉与血的纽结:培根与战后英国艺术研究》;另有“坚守与更新: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平庸时代”,“疾病的隐喻:欧洲当代绘画研究”,“被剧场性腐化的感性:论雕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契机”等30余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美术》《美术观察》《世界美术》《雕塑》等国内外核心刊物。独立策划多场学术展览,自2014年以来作为国际、国内多个大型艺术展览学术主持,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学术理论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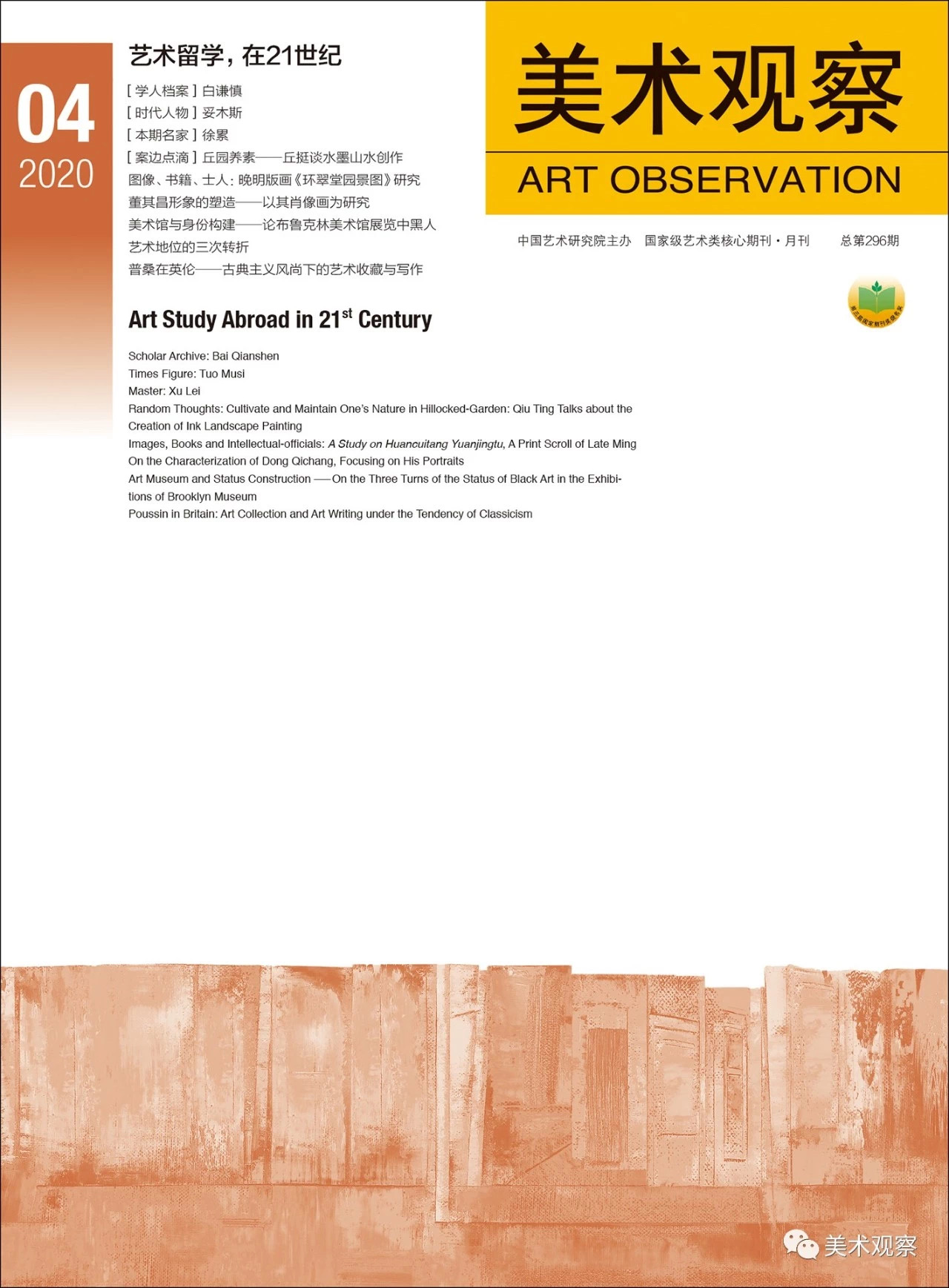
原文发表在《美术观察》2020年第4期
原文题目为:安尼施·卡普尔与当代艺术的肉身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