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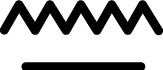
“写意”是我们的共同理念
○
文/ 郑工
“精神”与“图式”,是首届中国写意油画双年展的两大主题词,而“写意”既在于精神也存乎图式。作为主题展区,主办方邀集了国内著名的油画家,以他们独具个性的作品呈现了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的基本面貌。步入这一展区,大家会看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无法预测。画面都是具体的形色关系,每个人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方式也不一样,可我们的问题是,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与图式存在?
何以为图式(schema)?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图式属于先验范畴,作为知性的概念潜藏于人的心灵深处,但能扩充到感性对象,对形式有所限制。后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却将图式看成人的心理内部一个可变的动态的认知结构,一旦外部刺激被个体同化于这一认知结构,便能做出相应的反应。作为画家,这种反应可直接导致图式的外化,在个体层面上体现为某种表现样式,那都属于个人的事。看来,图式的“动态的可变性”十分重要,个体的同化与外化作用也十分重要。讨论油画的图式,在历史层面上,应该从作品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或某种样式去询问内在的心理认知结构,询问文化的主体性。那么,我们就不会将图式限定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文化圈,不会将图式固化,也不会认为油画就应该是曾经的那个样子。经典的意义在哪里?在于能说明过去,能很好地证明曾经存在于主体内部的认知结构,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观看世界,并通过怎样的方式去表现对象。身处当下的我们,是否也应该为后来留下明证,证明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绘画 去观看世界,表明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图式。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为后来创造经典,这是我们强调图式存在的第一层意义。
图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共有的心理认知,而范式(paradigm)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的信念,表现为共有的研究意向,界定关注的对象及问题的范畴,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并能提供范例。作为油画家,可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认知结构基础上形成个人的表现样式,可作为画家集群,也是文化共同体,“中国写意油画”是否能向学术界提供范式,表明我们的学术态度与艺术主张?尽管参展的这些画家是写意油画探索实践的成功者,他们的作品富有启发性,在油画语言创新性发展问题上也展示了各种可能性。但这种个体实践只是图式的外化,其作品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作为学派的存在,我的注意力还在于其中是否存在“范式”,即在形而上的思辨层面上为我们展示共有的信念?显然,“写意”是这一展览或这一学派的核心理念,也是由个体图式转向集体范式重要的概念工具。
我们不能将“写意”这一概念狭隘化,以为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风格或手法,甚至将其与“写实”的概念相对应,寻找其意义边界。作为观念形态之“写意”,其概念的涵盖面要宽很多,在艺术界,可以有“写意雕塑”“写意戏剧”;在生活中,可以有“写意空间”,写意性似乎成为东方人审美的一大特征。这是“写意”概念的横向面,而在绘画领域还有一个纵向的展开面,可以对接中国绘画的历史传统,承续其人文精神,前述宋元,追问汉唐,乃至于问道先秦,在新石器的彩陶中让我们领悟绘画存在的元初意义。作为学派范式的核心理念,这一历史的纵向深度可以增强新范式的社会学内涵及其构造功能,但能否由此触及元范式(meta-paradigm)却是问题,这涉及到文化的质性研究。依据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但科学的具体性却不容忽视,因为范式是某一科学集团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在一定的学术论域中表明其研究意向,为新传统的出现提供一套模型。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替变。可见,任何范式都有自己的论域,也都占据相应的历史时段。对于“写意油画”而言,在油画艺术领域,尤其针对欧洲油画的传统就具有变异性,意味着一个新范式的出现,而对中国绘画的传统,却有着一种延续性,不仅是精神的延续,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也有延续性,同时也存在着变异,也意味着一种新范式的出现。这是我们强调图式存在的第二层意义。
如果将“写意”视为写意油画学派的共同理念,那么,个体性的阐释及互为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必然涉及每个人对材料和技法的不同选择,在方法论上不断调整与补充,进而在艺术语言的本体问题上加深对“写意性”的理解。展览就是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例证。这一展区共有56位画家的100多件作品,是否每一件作品都可以成为例证?或者每一位画家都可单独为证?现有的答案只能落在后者,以画家单独为证,讨论画家的个体性及其相关的写意性表达。若强调互为阐释,却又将我们的目光落在个体区隔与相互间的过渡状态。我们能否以此建立一个研究序列或阅读序列,看看写意油画学派的学术论域到底有多宽?
这一问题的难度较大,难就难在这一学术群体所采取的开放性姿态,使其边界较为模糊。比如偏向写实风格的有曹新林作品《嵩县老人》,偏向抽象风格的有鸥洋作品《觅空》。这两位画家在这一群体中年长一辈,鸥洋是1937年生,曹新林是1940年生,两人均于上世纪60年代就学或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37年出生的李秀实,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在画“墨骨油画”;1941年出生的杨尧,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1944年出生的邱瑞敏,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讨论写意油画的范式系列与个体区隔,作品的风格是划分的主要依据,而作者的年龄与教育背景是重要的参照系,由此可以生发出许多新的议题,会涉及到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地域间的差异。这批三四十年代生人,在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年,他们思维活跃,变数较大,都有自己坚守之处和新的探索。而五六十年代生人,那时还是青年画家,思想较为激进,批判性强,转型也快,故在这次主题展中依然扮演主角,人数最多,其画风多在具象写实与抽象表现之间,强调绘画的“写意性”,而不怎么采用“具象表现”或“表现主义”等来自西方的概念。可见,80年代对这两代人的影响都非常大,通过近二十年来不断的探索,他们澄清了认识,对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们之间,若论个体图式均已成型。
面对这类情况,要回到“写意”的观念上讨论其区隔与系列关系,只能在集体范式上区分几个不同的发展维度,或者将一些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概念互为阐释,形成整体的论述。如形式、形态与形象,有区隔又有联系;又如微观与宏观,有区隔又有联系。相互之间交集最多的地方,就是范式的核心区,也是概念分化与整合最为活跃的区块。为此,我们可以为范式理论确定其目标、进行预设,找寻方法,形成研究框架。通过展览展示其个体性图式,是为研究集体范式做准备,这是我们强调图式存在的第三层意义。
强调图式并非忽视精神。在学术建设方面,有些观念必须明确界定,有些理论必须系统化,需要将问题落实到一些可供分析的事实上,避免似是而非的论争。作为学术范式的最终形成,一般经由三个阶序:第一,在旧范式的基础上构造新范式并推出成功的案例,具备一套可行的方法与相关路径;第二,在相关的学术群体获得普遍的认同并形成一种习惯与传统,在社会上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展示其新的发展趋势;第三,在思想层面上获取新的观念。相对于此,我们的理论建设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相互认同的同道,有了一批成功的创作案例,而展览就是一种推广的方法与路径,在长春落地的双年展就是很好的学术平台。谈论图式,恰恰是目前最适当的话题,能承接理论与实践,也包容着精神。精神是无所不在的,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现在,以观念性问题替代精神的言说,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
2019年11月7日于北京
《精神·图式一一首届中国写意油画双年展》
主展区部分参展作品:

《层林尽染》 范迪安 油画 400×140cm

《仿扫地式》 戴士和 油画 80×80cm

《梦幻金秋》 宋惠民 油画 120×80cm

《在那高山顶上》 闫平 油画 200×180cm

《北京密云古城》 贾涤非 油画 81×65cm

《春满枝头》 王克举 油画 140×160cm

《叶子红了》 张路江 油画 200×140cm

《铜鼓岭的礁石》 邓平祥 油画 120×160cm

《山水·三》 段江华 油画 100×80cm

《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新城》 叶向明 油画 80×60×2cm

《黄河之一》 王琨 油画 138×80cm

《多彩的世界——朋友圈》袁文彬 油画 200×200cm

《船》 孙立人 油画 120×110cm

《陕北之三》 王辉 油画 150×150cm

《悠系列之二》 张新权 油画 100×80cm

《郊外的葵花地》 王建国 油画 180×200cm

《城堡》 管朴学 油画 180×140cm

《长白晴雪》 刘兆武 油画 240×120cm

《礼赞青花瓷》 任传文 油画 165×145cm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孙建平 油画 360×210cm

《昨夜星辰昨夜风》 李秀实 油画 85×65cm

《落霞渔归》 王力克 油画 150×150cm

《龙王塘渔港》 包泽伟 油画 100×80cm

《悠悠鹿鸣》黄礼攸 油画150×100cm2018年

《诺夫格罗德教堂》杨尧 油画 60x40cm

《皖南祠堂》 邱瑞敏 油画 100x80cm

《白夜》赵培智 油画150X300cm

《网与船》 张立平 油画 190x200cm

《行·系列B512》 文祯非 油画80x100cmx2

《回家》 砂金 油画 100X80cm